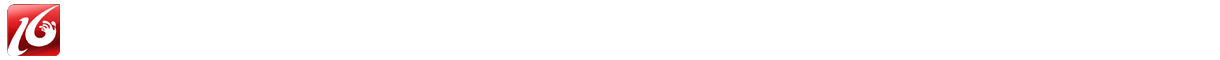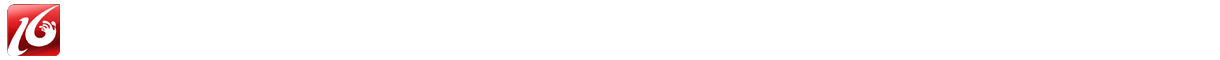克拉玛依日报讯(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张冰)近日,阿克苏杯·第八届西部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阿克苏市举行。克拉玛依市作家朱凤鸣的《去旷野吧》和毕鸿彬的《啼血相思》分获散文奖和纪实文学奖。
颁奖典礼由自治区文联、阿克苏地委宣传部主办,阿克苏地区文联、《西部》杂志社承办,阿克苏地区融媒体中心、塔里木传媒集团协办。
西部文学奖是《西部》杂志社于2009年设立的期刊双年奖,是新疆汉语言文学的最高奖,也是新疆设立的首个面向全国的文学奖。西部文学奖迄今评选了7届,共有80余位来自全国的作者获得殊荣。本届西部文学奖获奖作品是从2022至2023年度《西部》刊发的作品中评选产生的,共有9篇(组)作品获奖。
朱凤鸣的《去旷野吧》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深邃的思考,引领读者走进一片充满自由与挑战的精神旷野。作品不仅记录了旷野中的生存状态与人文景观,更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伟大。授奖词评价其为“人与自然博弈共存的时间简史”,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诠释。
而毕鸿彬的《啼血相思》则以深情的笔触,追忆了40年前那群在天山脚下以青春和热血筑就新疆交通动脉的筑路官兵。作品通过广泛深入的寻访与细腻的文学叙事,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现于读者眼前,展现了建设者们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与眷恋,令人动容。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石油作协副主席、克拉玛依市(石油)作协主席申广志说:“朱凤鸣与毕鸿彬两位作家的获奖,不仅是她们个人文学创作的成功,更是克拉玛依市乃至新疆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证明。我们期待更多本土作家能够以此为契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体现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为新疆乃至全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更多克拉玛依力量。”
相关阅读
《去旷野吧》(节选)
●朱凤鸣
旷野有风,有时候很温柔,有时候很暴烈。
夏日的下午,阳光热烈,旷野里没有风,只有红柳树上蝉的密集的嘶叫,间或一两只声音粗哑的鸟鸣。远处突然卷起了一个风柱,裹挟着沙石的风柱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四野空旷,无处可躲,只好站在原地闭上眼睛,等沙柱卷过来沙子打到身上,再离开,眼看黄色的沙柱在远处变小、消失……
二处
我小时候就住在旷野中。
我居住的那个地方叫二处。二处以前属于新疆兵团工二师十三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石河子派到克拉玛依油田支援油田建设,就留在油田了。二处最初只有相对的两排土平房、一个连队食堂。父母的工作现在看来也很简单,在砖瓦厂烧砖、筛沙子、上山打石头,到各油田区域和水泥、盖采油用的房子,挖一段又一段深长的管道,全部是纯手工劳动。
为了改善生活,家家都养了鸡或兔子,邻居家喂过羊,我们家有一年甚至还养过一头猪。爸爸在家里挖了一个地窖,真的是地窖,并没有往里放菜,那时中苏关系不好,他说打仗时就钻进去躲着。后来搬到红砖平房,才挖了菜窖存菜、放西瓜。
从我家出来往北走,穿过公路和树林不多久,就有成片的雅丹地貌,只是地势平缓,不如魔鬼城那般深峻、规模宏大。
二处人在周边种了很多树,中学周围尤其多。我上学时偶尔几天发奋图强早起去学校操场跑步的时候,周日假日早晨到校园教职工房子那边的围墙外游荡的时候,都能听到男声或女声“咪咪咪”“啊啊啊”练唱的声音,显得格外热闹。离开学校以后,我再也没听到热闹的美声练嗓的声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油建一分公司也就是所谓的二处整体搬进城,我家也搬到市里,从此二处这个地方被废弃。我有时候想,当年父母在油田的那些工作都是重体力劳动,二处人的贡献和功绩在油田建设过程中几乎微不足道,不像勘探、钻井、采油那么引人注目,有着轰轰烈烈的故事。父辈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印记,在时代的车轮中几乎无从留下,正像那句泰戈尔的诗句“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然而我已飞过”。即使风沙湮没了历史,它仍然存在。
风
两排土平房临近公路,公路北侧种植着树林,树林挨着一条水渠。除了低矮的灌木,周边什么都没有。
旷野的风从远处吹来,又奔向远方。
那时候的风可真多,刮大风的早晨,父母不用上工地,全家人紧闭门户酣睡。风停后开门扫院子,妈妈生火做饭。现如今,日日忙于工作和家务,真是怀念那时,睡觉中途醒了、听风呼啸又继续呼呼大睡的时光。
大概是1980年,我家搬到离土平房几百米远的红砖平房,那时二处人已渐渐多了,分出三连、四连、五连、六连、砖瓦连,甚至有了小学、中学、俱乐部、医院。
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条纱巾,记得我的是深粉色,起风时立刻用纱巾把头包住往家走。不包纱巾的话,沙子打在脸上疼,眼睛也睁不开。多少次上学或者放学路上,我都包着那条粉色纱巾,低头弓腰顶着风走路。那条深粉色纱巾现在看起来土气得要命, 我却非常喜欢,包头蒙眼睛的时候,目之所及皆是粉色的世界,粉色的旷野戈壁,粉色的土墙院子,粉色的风。
二处往南有很多农田,农田中间种了一排一排的树间隔挡风,有的还把苇把子糊上泥做成一堵墙,用来帮农作物挡风。麦子收割以后,大人们约着去捡麦穗,搓了皮和大米混着煮粥,一屋子香气。当然小孩子喜欢的,是嚼生麦粒,抓一把塞进嘴里,嚼着嚼着变成了泡泡糖,可以“叭叭叭”地吹泡泡。
上学以后,才知道克拉玛依还有个名字,叫风城,因为风又多又大。现在风城特指有魔鬼城的乌尔禾区,那儿有一个以采集稠油为主的单位就叫风城作业区。1984年一场大风,刮倒了电厂半面围墙,全市停电三天。我也曾经站在阳台上看到风暴起时瞬间把林带里的树刮断。我妈是家属工,也上油田挖管沟挣钱,她说有一次下班回家路上遇到大风,她们坐的东风汽车侧翻,一车的家属工都掉落到地上,竟然没人受伤。
沙
旷野空旷,天穹如盖。
我渐渐长大,越走越远。往南是大片的戈壁滩,有一些梭梭、红柳、沙拐枣之类的草甸植物,早些时候没有煤,父母要在周日推上平板车,到戈壁上去打柴。父亲说梭梭最好,耐烧。后来有了煤,冬季来临时,家家在院门边砌上砖囤煤。我们喜欢在炉盘上烤馍馍片,烤出来又酥又脆面香味十足。等我上初中的时候,早有了液化气罐,后来又通了暖气,连煤都不用了。
南戈壁靠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沙子的家乡。早先父母从事油田建设工作,有一项工作就是筛沙子,一锹一锹把戈壁里的沙子抛到细网筛子上,筛出大小均匀的建筑用沙,在南戈壁能见到很多白色的螺旋形小贝壳,我猜想,很久很久以前,南戈壁就是一片大海。南戈壁还有很多很大的沙堆沙坑,沙子一波一波像波浪。我特别喜欢脱了鞋子在沙浪上踩,风吹过细沙升腾氤氲犹如轻柔的浪花,仿佛置身大海。
……
有车以后,去哪里都近。从沙漠公路去南戈壁也就十来公里。我从家到小拐乡附近的沙漠看开花的异翅独尾草,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足够。从二处到后山,如果算直线距离,估计最多也就二十公里的样子。从市区穿过整个后山到铁厂沟,也就九十公里,就算是走S201省道,最多就一个半小时,如果是从G3014高速过去,要不了一个小时。然而,旷野并没有因为这些路而变小,站在后山往下望,整个克拉玛依市,有炼油厂和储油罐区的金龙镇,也就只占了一小块地方。旷野茫茫,四极八荒,大着呢。
我已经很久没去旷野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扑入旷野宽广的胸膛,站在长了很多梭梭柴、沙拐枣的荒漠极目四望。秋天来了,那些郁郁青青的低矮灌木上晕染着一团团深深浅浅的黄与红,已经干枯的小甘草在风中轻摇,一切都在斜阳的照耀下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晖。灰蓝色的后山在金色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浓重的紫金色。
久违了,旷野!久违了旷野里风的歌吟,久违了旷野的虫鸟低鸣,久违了这穿过我身体的风。天高地远,旷野宽阔而庄严,雄浑而壮美。
前两年流行起海来阿木的歌《别知己》,我听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月亮冷冷地挂在天上,它也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离别,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跳起舞来,趁着酒意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
这欲悲欲喜,是我的,是篝火的,也是旷野的。
作者简介

朱凤鸣,70后,土生土长疆二代。系新疆作协会员、中国石油作协会员、克拉玛依市(石油)作协常务理事。就职于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喜欢花花草草,喜欢读书,喜欢慢时光生活。创作的散文、评论等作品先后发表于《散文》《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西部》《地火》《新疆日报》《新疆人文地理》《散文百家》《延安文学》《福建文艺界》等报刊。
获奖感言:
愿用一生为这片土地创作
●朱凤鸣
俯瞰北疆,可以清晰地看到辽阔大地的纹理和呼吸。每当我坐飞机经过博格达山群,站在某处山坡或高地,眼前这种裸露的大地的地势和纹理,辽阔壮美,总让我有着难以言喻的感动和赞叹。犹如道家修炼得道,站在天际俯瞰人间。
克拉玛依坐落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它其实是在从群山到盆地底部的缓坡上。往南,面对浩瀚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面背靠着的,则是后山。我小时候,听说这座山叫成吉思汗山,后来听收音机里说,专家考证这座山和成吉思汗没有任何关系,更名为青克斯山。等我长大后忽然得知,这座山又改名字了,叫加依尔山。我最近才了解到,我们认为的所谓的后山,其实是多座山组成的山系,包括加依尔山、萨吾尔山,向北一直连到阿勒泰山,向南则连接到博乐的阿拉套山。如果开车沿老217国道跑,后山则会一路陪着我们。话说前几天,我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写一写我们的“大靠山”——后山。但是这个念头刚起,因为得知获得西部文学奖,我回头再看我写的《去旷野吧》,发现其实自己已经把后山写得差不多了。
从小看着这片土地的山水戈壁荒漠,和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草木、人们,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在领略它的美,感受身边的悲欢喜乐,哪怕一棵盐生草、哪怕一株假木贼,哪怕早已枯涸的古河道……这片土地如此辽阔,值得我用一生去热爱,为它去记录、去写作。这次获得西部文学奖,完全是意外之喜。这让我深深地觉得,这片大地是我的宠儿,而我是《西部》的宠儿。我愿意继续用我的心我的笔,去记录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动植物、人和事,让生命由此而更加饱满、生动。感谢《西部》给我的奖励和鼓舞。
《啼血相思》(节选)
●毕鸿彬
一
远处青灰色的山立在天边,一路陪伴着我们。虽然是6月,绵延如齿的山顶上依然裹着积雪,有些地方与白云融为一体,看上去山比天还高。我们的车队向着天山进发,公路剑一般劈开戈壁,直指山腹。
老兵们望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发出感叹。40多年前他们就是从这里朝着天山挺进,打通了独库公路。当年筑路的年轻战士们并没有全程走过这条路,如今已入暮年,重走在曾经建设过的路上,怎能不激动?
坐在近旁的曾昭英一直缄默不语,出神地望着远处巍峨的山脉。我知道她内心有一泓波澜起伏的湖水,浸润着45年的梦想,从1976年到2021年。现在我们都走在圆梦的路上。
虎视着我们的山脉是天山支脉依连哈比尔尕山,哈萨克语意为“肋骨”,它长在北天山庞大的骨架上,是独库公路要穿越的第一道屏障,随后还有阿吾拉勒山、那拉提山、科克铁克山、秋里塔格山。这些排出连环阵的道道山脉,怀揣 4个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达坂,随时会抛出危险威逼翻越山脊的公路。这条路位于天山中部,起于北疆独山子,终至南疆库车,全长约563公里。公路蜿蜒舞动于天山南北,跨越5条天山主要河流,如一条彩练,将许多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披挂其上,集险、俊、奇、美于一身,堪称“全国最美公路”。这位公路骄子,沿线地质脆弱,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雪崩、塌方、泥石流等公路病害频发,又被称为“中国公路病害博物馆”。
我第一次走独库公路是1993年,也是6月,仅是翻越第一个达坂哈希勒根去乔尔玛游玩。那时只知道这是条国防战备公路,对它几乎不了解。路上见一辆车被山上滚落的石块砸坏,而崖壁上猩红的大字“老虎口”则在以后的回想中冒出阴森的寒气。那次出行,早晨穿着单衣,几小时后到达达坂竟大雪纷飞。重穿一回棉衣,才真正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神奇。那时我并没有想到,26年后能和这条路结缘,和筑路官兵结下深情厚谊。
当年整日与石头打交道,衣服磨得到处是破洞的官兵也没有想到,40多年后,这条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并成就了一座博物馆。2019年,当他们中的许多人听说要在独库公路零公里处建独库公路博物馆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满含深情地说:“感谢你们没有忘记我们,新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见到你们就见到了故乡人。”为了征集物品,还原这段历史,我们从疆内到疆外寻访筑路官兵,从老兵们的讲述及大量资料中,捞出这条沉落在发黄卷宗里的路,抖落久积的灰尘,让它变得清晰起来。
这条路缘于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搞活天山”。毛主席站在巩固国防、保卫边疆的高度,大胆构想打通沉睡亿万年的天山,结束新疆自古以来南北疆之间行路难的历史。最初任务交给了在疆的部分陆军和民工。面对天山苍苍莽莽的群山,筑路无疑愚公移山、困难重重。军民苦战数载,工程最终告一段落。
1974年4月,军委工程兵一万三千人奉命挥师进疆,向渺无人烟的天山集结,开始开山劈路。十载春秋,历尽艰辛,终使天堑变通途。1983年9月,独库公路全线贯通,南北疆的路程由一千多公里削减近一半,由过去耗时四天折成当天就能到达。军民欢唱,群山荡歌,这条具有非凡意义的公路,以至少168名战士的牺牲和数千人负伤致残为代价,以“六里一英魂”的悲壮,在中国公路建设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在乔尔玛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上,曾昭英的爱人李善国的名字镌刻在第二位,她把思念也深深刻进了岁月深处。
二
2019年8月的一个下午,退伍老兵杨志轩在我的办公室捐出了当兵时的机械操作手工作证,我由此一步步走进筑路官兵这个群体,走进这段翻飞着血色落叶的时光隧道。
修筑独库公路的这支工程兵部队是师级建制,主力由三个团组成。1974年5月,官兵们从长江边的宜昌三峡莲陀出发,奔赴新疆。铁流滚滚,一路向西,经过8天闷罐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坐数天汽车到各团驻地。部队摆开龙门阵,分段从南北两端相向施工,每个团都承包了建一条隧道的任务。部队当年就开始施工,进入天山后,正如战士们所言,“吃尽了人间所有的苦”。
说起“苦”,山风就开始喧哗。如线的公路,百分之六十在崇山峻岭、深涧峡谷中攀爬,五分之一凿在悬崖峭壁上,施工极为困难。曾有一张照片,一名战士腰系安全绳,吊在打入悬崖绝壁的钢钎上,手拿长过身躯的钢钎悬空排险,脚下是万丈深渊。公路一半以上路段在海拔2000米以上,高寒缺氧,大雪封山长达半年,雪崩频繁。恶劣的环境下,棉袄一年四季不离身,许多人落下关节炎等疾病。
在山上只能住帐篷,寒夜冻彻肌骨,被子上加盖皮大衣还冷得瑟瑟发抖,战士们就把洗干净的破帐篷、麻袋再盖到皮大衣上。帐篷内仅靠一只火炉烧柴取暖。深夜炉火燃尽,温度很快下滑到冰点以下,一条条冰溜子吊在帐篷外。早晨起来,鞋子往往和地冻在一起,要用镐头刨出来才能穿在脚上。“苦”的画面徐徐展开,大雪纷扬着落进老兵的梦。
苦涩含在嘴里,不得不吞下肚。常年喝的雪水,飘着羊粪和尘土;吃的压缩干菜,纸一样缺少营养;一封家书在路上要走一个多月,许多人收到家中亲人生病的电报或信件时,亲人已经离世。
“这条路是我们用双手一点点抠出来的。”老战士们说。
凿山开路要挖导洞,在山体上向内挖一条直径约一米的狭长洞穴,再在两边挖出药室,填充好炸药进行爆破。导洞内空间狭小,粉尘污染严重,战士们很快成了土人,除了牙齿还能分辨。照明用的马灯常因缺氧熄灭,许多人晕倒在洞里,被战友拖出来。抢救醒后,又冲进洞里。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终生忍受的矽肺病,是苦过的证明。
说起“苦”,眼泪就更加咸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候下施工,绿军装冻成银铠甲,大头鞋结成冰疙瘩。全线建三座隧道,个个险象环生,不亚于一场场生死搏斗。隧道潮湿,洞顶不断有雪水渗入,加上内外温差大,官兵们进洞一身水、出洞一身冰,棉衣棉裤冻得硬邦邦,胳膊和腿都打不过弯,得挪着回驻地。二十多位战士,生命之火被命运无情的手摁灭在阴暗的隧道里。
战士们曾写过一副对联: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圆!这是他们的心声,每当说出这一心声,“7·15”大塌方就被重新回放。
作者简介

毕鸿彬,1967年生于新疆。1987年参加工作,就职于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从事过技术、管理、政工工作,近年担任过独山子博物馆、独库公路博物馆馆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现为新疆作协会员、中国石油作协会员、克拉玛依市(石油)作协常务理事。作品曾在《西部》《绿风》《伊犁河》《石油文学》等刊物发表,并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收入丛书,出版个人作品集一部。曾获第五届中国石油职工艺术节文学大赛报告文学三等奖、克拉玛依黑宝石文学奖、独山子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奖项。
获奖感言:
只顾耕耘 莫问收获
●毕鸿彬
我来自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它是全国重要的石化基地,也是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我的获奖作品《啼血相思》正是书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筑独库公路的筑路军人中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我想,如果这些筑路老兵和他们的亲属知道这一消息,一定会和我一样对《西部》说声“谢谢!”。因为他们对这条路感情深厚,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他们付出了青春、血汗甚至生命。没有他们,就没有独库公路,就没有这部作品。
当我得知获奖的消息时,我的内心是不安的。一直以来我在写作上都缺乏自信,根源是,我并非才高八斗、见多识广,也没有那么足够努力。在我眼里,《西部》是一座高峻的雪山,在它面前我矮小而虚弱,能在它身上留下一个脚印都令人欣喜,更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够获奖;然而,它却以草原的宽阔胸怀接纳、滋养文学爱好者,让我不断获取攀登的力量;它又宛若一汪恬静的湖泊,给予干渴者暖流。
本次获奖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激励。我长期在独山子石化企业工作,受着石油精神的熏陶。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寻访到许多筑路官兵和他们的亲属。深入到这一群体后,我听到了许多有关使命忠诚、生死考验、奉献付出、亲情爱情的故事,因而被天山筑路精神深深打动。一路的行走让我萌生了书写的冲动,但我自知笔力不足。我曾对母亲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好?她说:“不要想结果,想写就去写,要多向别人学习。”我八十岁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眼疾和心脏病,在我陪她去内地养病期间,我借来的文学书籍还未细读,她已不思茶饭地读完,那是她生前读的最后两本小说。她朴素的话语是要我怀有一颗“只顾耕耘,莫问收获”的平常心。我要向更多的人学习,也要向我的母亲学习,对所爱报以真诚。
感谢《西部》对我这篇作品的认可,让我有了自信和前进的动力。我希望今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一场修行,炼笔,更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