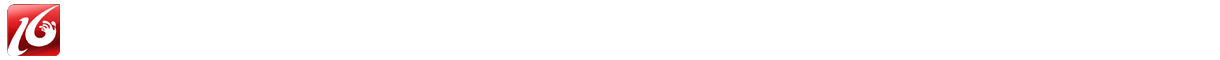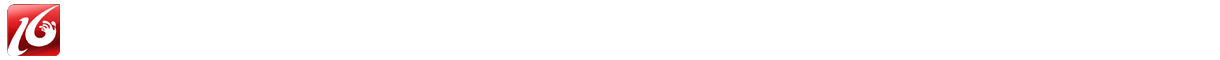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刘仪(永安公司)
雄鹰有飞向蓝天的梦想,有搏击万里长空的斗志。人一样有征服高山的欲望,攀登高山是一种神往,征服是人的本性,人的一生都是在攀登一座山峰。我的故乡就有许多大山,小时候的我喜欢去攀爬,总要望着高山的山顶,想象上面的神秘,爬上山顶是一种征服,更有胜利的喜悦。我从故乡的大山走出来,去攀登外面的山峰,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次旅行和冒险?
那年,不到二十岁的我怀揣着一颗梦想的种子,背井离乡,从南方的春天出发,去新疆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从我家出发到新疆克拉玛依有3000多公里,走这么远的路,我还是第一次。
那年刚过完年,正值南方的春天,我把自己这颗小小的种子,小心翼翼地带在身上,第一次出远门,就怕丢了。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要去的地方会是什么样,我憧憬着一个春暖花开的春天。
那时候,坐火车出远门非常艰难。一到春天,进城务工的人就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火车站人山人海,买票得排队,吃饭得排队,上厕所得排队。有时几天蹲在车站都是一票难求,买不上票,最后只得向高价妥协,虽是一万个不情愿,也只得认了。
火车上同样人挤人,车厢过道、厕所门口,没个空地。站着的,坐着的,还有躺着的,都挤在一起,像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各种方言的说话声,婴儿的哭声,全都混在一起,像是跑调的大合唱,又像是海面卷起的阵阵涛声,一浪高过一浪。只有到深夜,大多数旅客都困了,才稍微安静一点,整个车厢忽明忽暗,微弱的灯光穿行在厚重的夜色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像波浪一样,随着火车一路奔跑。
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的村庄,我熟悉的大山、沱江,还有我儿时的河流,我的亲人、炊烟,他们就像一块沉重的磁铁,被火车无情拉动着,一路向北,将南方的春天甩在身后。
火车一路北上,车窗外的景象越来越荒凉,夜晚就更孤独了。车厢里鼾声如雷,掺杂着各种怪异的声音,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我睡不着,晕晕沉沉坐在地板上,心里只想着快一点到站就好。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被荒凉压制住,它们像是追风的萤火虫,跟着列车一路前行,穿过荒凉的黑夜。行走在黑夜的列车是孤独的,像一条巨蟒,扭动着长长的身躯。只有列车到站临时停靠,才能见到裹着厚重棉衣上下的旅客。兰州的灯火就像荒凉中聚集起来的火焰,让我感到意外,几天来,我在兰州站看到了最大的城市,然后仍是一望无垠的荒凉。
终于在五天后,火车到达乌鲁木齐车站。一下车,冰冷的风像刀子一样掠过脸上,踩着厚厚的积雪,我又马不停蹄地坐上客车,前往克拉玛依。
在217国道行驶几个小时后,客车到达克拉玛依车站。已是傍晚,天色灰暗,飘着零零星星的雪花。一行人扛着大包小包走在街上,刚开始还较整齐,走着走着,就各奔东西消失不见了。
街道冷冷清清,偶尔经过几个人,也是步履匆匆。路上的积雪无人打理,有几厘米厚,人走在雪面,会发出清脆的咯吱咯吱声,像踩在席梦思床上。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偶有大货车缓慢驶过,从车尾吐出老长的一条白烟,缓慢飘散,跟着车轮卷起的风在雪地上打转。树就更少了,几乎没有一根直树,树都面无表情地倾斜,凌乱地晃动着僵硬的枝条,像半身不遂的一个人躺在路边。顺着一条路望去,三四层低矮的楼房支撑起一座城,隐约可见远处的土坯平房顶上,直立的烟囱向天空冒着整齐划一的白烟,没有风的打搅,那种直,简直像是尺子拉出来的。偶遇路上蹬着自行车的行人,他们都把头蒙得严严实实,只露出来两只睫毛上沾了雪花的眼睛。一切景象,都是那么陌生,那么冷酷。一座城市并没有因为我从南方到来而变得更加有趣,但我要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我不知道一座戈壁滩上的城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里没有天然的河流,没有可以利用的天然农田,这里有的是常年风沙,干旱少雨,严寒酷暑,为什么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建一座城,是我一来就有的疑问。
克拉玛依的春天是激烈的、瞬间的、来势凶猛的,住在平房的人最能感受得到。夜晚,风像幽灵一样降临,只听得窗外噼里啪啦,大门即使加了支撑,还是像有人在使劲推、抡起石头使劲砸,这是我在南方没有见过的场景。我能感觉得出来,肆意的风,像发疯的狮子,正在席卷一座城。
知道“克拉玛依”的意思,就能知道这座城市的来历。黑油山,就是油苗露头的地方,山上常年往外流油,聚集起一座天然油池,千万年的流淌形成了“沥青山丘”,山上不长树不长草,却“长”黑色石油。
黑油山上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池黑油,终年冒着油泡,像春天的花骨朵。黑油山的冬天,落下的雪没有任何保护,一场风就刮跑了。没有了雪的黑油山,光溜溜的像个拱起来的土包,一池油花完全暴露出来,跟着油池淌出来一条小溪,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远远地看,就像春天融化的雪水。因此,黑油山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些。
要不了几日,城市里的树开花了。街头巷尾、公园角落,红的桃花、白的李花、粉的海棠花在枝头上挤得满满当当,春天似乎住进了城里。而戈壁滩上,还是光溜溜的不见绿叶花草。春天,我喜欢沐浴在阳光里,感受不一样的温暖。城市的西边也有山,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山上都是形态怪异的石头。躲在石缝里的残雪,望着外面的阳光泪眼迷茫,骆驼刺和梭梭草是戈壁滩上最常见的植物,它们常年被风沙侵袭,还要忍住干旱,要站住脚,得付出多大的勇气,就像油田上的石油工人,长年累月走在风沙里,在戈壁滩立起来一座座井架。
走在黑油山上,极目远眺,有一种无尽遐想的感觉,使人顿时胸怀宽广,诗意澎湃,这激烈的诗与远方的碰撞,犹如大海翻腾的巨浪,一次次从黑油山喷薄而出,涌向广阔的戈壁。是戈壁、是石油,是井架、抽油机,是这里的风,把我淹没在浩瀚的沙海里,顺着春天的通道,我漂向天山的岸边。等我回过神来,戈壁滩突然有了绿叶红花,仿佛是一转眼就发生的事情。骆驼刺长出绿叶,太阳花动情地开了,一些小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蜥蜴一般单独行动,像一截枯死的木头,很少见到两只或数只在一起。蜥蜴奔跑的速度非常快,贴着地面摇摆着身子,像水面上的快艇,要是被逼急了,能一个蹦子飞起来。暴晒在阳光下的蜥蜴,眼睛360度转圈,仰起它的小脑袋,肚皮对准阳光,抬起一只脚,让阳光晒到它的花白肚皮,那样子非常滑稽搞笑。蚂蚁这种小动物成群结队,它们以数量取胜,戈壁滩上黑蚂蚁多,个大,它们是怎么生存的呢?冬天大雪覆盖,夏天阳光暴晒,还要提防沙尘暴,一阵风,就有可能摔出去几公里,甚至更远回不了家。估计是我担心多了,蚂蚁有6条腿,别看它细胳膊细腿,身子可灵活自如,尤其是那个安装了天线的小脑瓜,更是灵敏。蚂蚁的腿既是脚又是爪子,遇到大的风沙,它们会趴下来,让身子更多地接触地面,用爪子紧紧抓住地面或者树枝。要是抓错地方了,那它就随风飘荡,跟着风滚落。但这不要紧,也不用担心,蚂蚁的身子就像弹簧一样,定能自由着陆、平安无事。春天,我见过蚂蚁喝融化的雪水,不光是蚂蚁,还有蜥蜴,它们都喝融化的雪水。当然,戈壁滩除了这些小动物外,还有大的动物,野骆驼、野马、野驴、狼、大头羊、野兔等等;还有天上飞的鹰,野鸡、野鸽子、沙燕等鸟儿,它们找到食物吃完后,喝几口刚刚融化的雪水,然后幸福地飞走。生活在戈壁滩上的这些动植物,冬天啃雪挨饿的艰难日子总算过去了,它们跟石油工人一样,迎来了美好的春天。
站在黑油山上,我在这忙碌而又安静的春天里,触摸到每一束细微的阳光、每一滴油滴,它们都有与我一样的呼吸。这里,每一根卑微的草,一只蚂蚁,一滴落入沙漠的雪水,都能让我找到生命的激情。每一朵风中摇晃的小花,都在给我灵感,都在激励着我前行,碰撞出鲜活的文字火花。这些年,我写石油工人,写一只蚂蚁、一只蜥蜴,从戈壁滩写到它们的生命。写到黑油山的一滴石油,写到一滴石油的生命,它们都是我活着的春天。
就当我是一滴黑色的石油,生活在黑油山的一滴黑色石油。我以为,一滴石油从地里长出来,一滴水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棵植物从地里长出来,一群羊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只鹰从地里长出来,一朵天上的云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滴石油。我沐浴在油池里,听大海的歌唱,每一滴石油都是一朵浪花,都是一首歌,一首诗,一段抒情散文。
一滴石油,带着我去探寻新的生命奥秘,在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个黎明,如一轮喷薄的红日,在浩瀚的沙漠戈壁,我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井架、一座油田、一条河流。那流动的激情,那澎湃的欢笑,从刚来的逃离到喜欢,到后来的留下来,到今天爱上一座城,到一首石油诗,都归于黑油山流动的黑色石油,它用永不枯竭的流动,绽放永不枯竭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