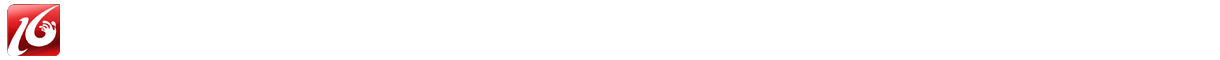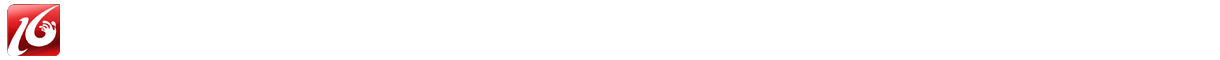六十多年前的这个日子,地质队在这儿定了井位。
那年的春风也像这个春天的风儿一样热烈。戈壁滩上的梭梭和苇草跟它们拥抱着呼呼哧哧地唱歌跳舞。
现在有春燕飞过来跟你挤眉弄眼,有密布的抽油机,有冲天的钻塔,有矗立的炼油炉,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有飞机场,有奔流澎湃的河流。它们在如海洋的风里划动,像赶海的渔船,像飞翔的雄鹰,像舞动的长龙,扬起风帆,展出翅膀,口吐悬河。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风吹石头跑,连鸟儿也不愿意飞过。
转眼到了火热的季节,一群年轻人过来了,他们才下战场,又上了战场。
他们用肩头扛,用肩膀拉,用双手搬,用头颅顶,用牙齿咬,用意志和精神拱,在亘古荒原上立起一座钻塔。他们要打一个千米深的油井,他们要从地底下钻出石油来,新中国的新型工业急需血液。
现在你觉得五千米八千米的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候,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真被人当作笑话。
人世间的事历来如此,神话总是在笑话中诞生,就像不穿裤衩也要造出原子弹一样,你只有把笑话变成了神话,笑话才不会是笑话。
所以,当别人把你当作笑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努力创造神话,你能够从笑话中创造出神话来,那你就是一个神话。
10月29日这一天,油井喷油了,高产油流,这里诞生出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
在一个接一个艳阳天里,烈日把太姥爷的脸庞烧烤成钢板。
宁静的夜晚,太姥爷踩踏着戈壁石向我走过来的声音有点像战场上的鼓点,红柳和苇草听到了总心潮澎湃。
太姥爷躺倒在我的身边,仰对着蓝天上的圆月亮发痴。风儿为他刮了一遍脸,云彩羞了他一把,被他身子压着的屎壳郎心烦意乱地骂了他一句粗话。你可别小看这些黑得像宝石一样的小虫虫,它们在戈壁滩算得是高贵的生灵,清晨迎着朝晖钻出沙堆,跑到骆驼刺那儿吸点儿晨露,倒立着露出屁股晒晒太阳,惬意了就在洁净的沙面上画出一幅幅图画。谁知道它们怎么生来就有这样的天赋,一会儿跳跃,一会儿奔跑,一会儿滚动,如永不言败的战车,像变形金刚,表演并不比蜘蛛侠逊色,甚至有如光头强和二熊一样让你忍俊不禁。
太姥爷对着圆月亮不断喊叫着太姥姥的名字,把月亮喊得向他越走越近。他是从心底里喊叫出来的,月亮一定听得如痴如醉。太姥爷是喊叫着太姥姥的乳名儿,那个醉人心肝的名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在戈壁滩死缠烂打的风儿听到了,梭梭和苇草还有骆驼刺早就心领神会,砂砾傻乎乎跟着痴呆,只有屎壳郎乐得像孙悟空一样乱翻筋斗。
丰收的季节里太姥姥就来了,太姥姥是这里的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批女人中的一个,太姥姥说她要在这里扎下根,从此她就是这座城的太姥姥。
夕阳西下,月亮圆如银盘,太姥姥和太姥爷就在我身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他俩互相叫唤着乳名,蛇儿交欢似地相拥着就躺倒在梭梭旁边那个沙堆上缠绵,紧紧地拥抱着不肯松懈。梭梭招呼着苇草快点儿捂脸,戈壁石都屏息了呼吸,圆月赶紧往王母娘娘的绸衫里钻,星星隐藏得不知去向,这阵儿屎壳郎倒是识相,它刻意要当这场大戏的幸运观众。
清晨,早起的太姥姥对着我的镜面梳妆,朝晖不失时机涂了她一脸重彩,蓝天恨不得扑下来当她新衣衫的布料。因为是春季,燕子在她的头顶上盘旋,燕子是太姥姥带过来的陪嫁,从此以后她会跟着太姥姥在城里安家。你不能贬低太姥爷和太姥姥的男欢女爱,那可是生命的神圣时刻,因为这样的神圣,才有了你的姥姥,你的母亲和你,当然因为神圣的继续,城市才会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