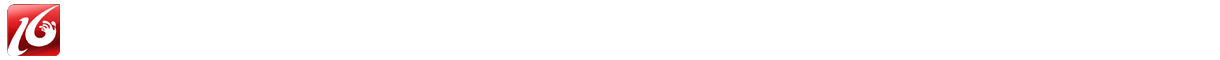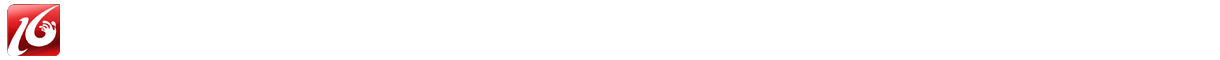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陶彩英(独山子石化公司)
11月22日,像蓄谋已久,像缘分使然,像天公作美,无数片雪花纷纷组团,轻驾戈壁山林间闲逛的北风,摇曳袅娜轻盈的身姿,以空阔苍茫的天空为舞台,飘飘洒洒成一场视觉盛宴。
大自然像彻底捋清了规则,又像重新洗完了底牌。不一会功夫,远处的山峰白了,脚下的路白了,行人的帽顶白了,松柏的枝桠白了,小区的楼顶白了。草丛、马路以及马路尽头,也都白成一片,纯洁干净,宁静柔和。目光所及,灰云沉重又低矮,压迫得全世界只剩一种颜色:苍茫辽阔的白。大人或孩子年复一年潜藏在心底对第一场雪的惯性热盼,从一双双睁大的、亮晶晶的眼睛里汩汩然溢出。那惯性的热盼里带着丰富多姿的表情、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打雪仗、堆雪人、溜冰、滑雪、赏冰灯,仿佛唾手可得的欢乐。也有些路人,脖子缩进肩膀里,驼背塌腰,帽檐遮住了眼眉,哈气模糊了视线,仿佛对初冬的第一场雪多少有些抗拒,又仿佛思绪纷飞,徜徉徘徊在秋天的舒适圈里,不能自拔。
刚下雪的时候,我看到三对野鸭相继降落到水库的水面。风起云涌,水波滚滚。野鸭们不怕冷,不怕风,也不怕雪。它们两两一对,悠然自得地啄食。不时地咕咕两声,互为应答,再回头相互之间望一望。我看不清它们的眼神,但我想它们的心里一定珍藏着深情。当别的候鸟迁徙远飞,它们却能靠彼此的慰藉、陪伴、照拂,靠自身强健的体魄、过硬的生存本领,坚守一方水土,繁衍生息。雪花组团亲临水库,轻舞飞扬,估计也是专门为这三对野鸭助兴的吧。
天色将黑,我又是夜班,就赶紧回家了。
凌晨2时出门,雪停。大门口已经堆起一拃厚的雪。我捧起一抔,好新鲜的雪啊,轻柔绵软,在灯光下晶莹剔透,闪闪发光。天空放晴了,不知道那么多、那么矮、那么厚实的灰云,都听谁的指挥,跑到高远的天边去了。一轮半月,像一轮弓,又像金元宝,金黄色,圆弧的弓形朝向大地,矮矮地悬挂在天空。我感觉搬个高凳,踩上去踮起脚,再伸长胳膊去摘,好像就能把它摘下来。又想到今天大夜班,得早点去巡检,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路上,雪有一定程度的融化,却在深夜升腾的寒意中,顺着车辙又结成一埂一埂的冰。车轮打滑厉害,我开车行驶得很慢。好奇怪,一路总共10个红绿灯路口,所到之处,竟然都是绿灯。难道初雪的大夜班上班路上,所有绿灯都有了灵性,变成护路使者,为保平安,巴巴儿为我而亮?
至北京路时,车窗外三四米处,与我并排行驶着一个外卖小哥。他驾驶电动车行驶得更慢。车轮在冰雪的路面上不时跳腾,他双手紧握着的车把,时不时划过一个S轨迹。每每这时,他的左脚尖也时不时地点一下路面,以找到新的平衡。啊,生活就是一场奔波,在春风里奔波,在夏雨里奔波,在秋霜里奔波,也在冬雪里奔波!我不也在凌晨两点的夜色里奔波吗?我多看了两眼外卖小哥,默默地与他擦肩而过了。
过了客运站,一路上的雪几乎被铲完了。路左侧有位环卫工人,穿着橘黄色的马甲。只见他手握一面宽阔的铲雪板,重复着弓步、起身,弓步、再起身的简单动作,正一大板一大板地将路沿石旁的雪使劲往榆树林中挥。他目光坚定,动作麻利,干得一丝不苟,充满了责任感,仿佛这条路上所有车辆的安全行驶都系在他身上。我忽然对他心生敬意:再简单的工作,用心坚持去做,变成社会价值,也会让一个人内心充满自信和尊严感,也会让旁观者觉得他是最可爱的人。我的同事们,也在这样的寒夜里,用手背揉醒睡意朦胧的眼睛,再穿起工装走向工厂。他们用手指试摸装置深处纵横交错的管线,用鼻子细闻空气中丝丝缕缕的异味,用耳朵聆听设备跳出正常旋律的杂音,用眼睛辨识高温下不同寻常的炉管颜色。他们的工作状态,偶尔被拍成照片定格成某些光荣的瞬间,被公诸于大众视线里。而更多更多的瞬间,只能成为他们自己职业生涯的自信和尊严,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也可能被年复一年初雪后的那半轮明月,装进心坎里,装进梦里,成为永恒吧。因为它是从几十亿年前的远古走来,又要向几十亿年后的未来奔赴。今夜初雪,与它而言,只是微微须臾间。
“老鹰门”很快到了。门外的初雪和门里的初雪长得一模一样;而我,却必须调整一下思绪,收敛起梦中遗留的感性,以最理性的姿态,昂首挺胸地走向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张冰
本期编辑:何沐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