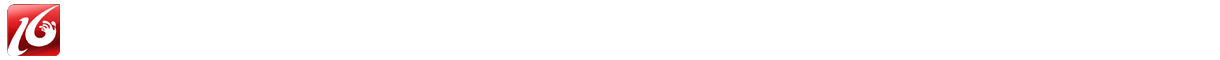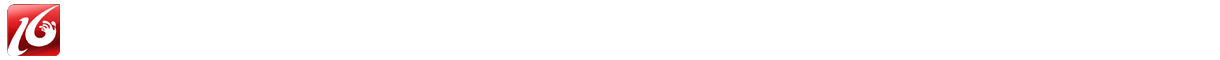组诗 | 郭志凌:石油密码
|
|
2024-12-18
|

●郭志凌(克拉玛依市锦绣花苑悦丰园)
风越擦,泪水越多
总有一种缺憾,
让青春搁浅多年。
不怪岁月,
迫使我们在人迹罕见的戈壁,
埋下憧憬的影子:一顶塑盔、一袭藏蓝、
一双工靴、一把管钳和单棉手套……
40年宽厚的一面墙,谁又能听见,
我抠进土里的手,在持续抽搐——
风越擦,泪水越多。
衰老的时光让我弄丢很多人的名字。
就记住了几个书籍上查不到的地名:
红浅、百联站、石西、夏子街……
从青涩到懵懂,就觉得往后只能和它们,
相依为命。
没想过分开,更没想过决别。
再冷的冬天,都不敢戴上手套。
我怕摘掉,会带下尚有知觉的皮肉。
头发稀疏,也不敢戴上帽子。
怕走失多年的工友,突然唤我的绰号。
勒在前额的符号,是一道油渍,
岁月恐怕都忘了随后的搓洗——
克拉玛依一号井
新闻里有一段旧闻的播报,
听起来很新,像没沾过水的衣裳。
绕着第一口油井矗立的住宅楼,
住在里面的人,
不知道与地基平行的位置,
是60年前,井场的布局。
不锈钢材质的油泡景观,
时光怎可能站稳?
游人投射的背影,
也扭曲不了历史的轮廓:
也许害怕记忆生锈,
涂装的油漆让井口上安坐的铸铁,
像喷油后,舍不得解下的红绸。
——一座依赖石油生存的小城,
一号井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老棉袄
一件被油裹紧,被风蹭亮的老棉袄,
崩掉的纽扣被麻绳取代。
没有干洗店。即使有,也不会接收
搓不动,类似金属的腌臜。
那时候,日子都过得拮据,
单棉两套工作服,
一年只发一次。
遇到井喷抢险,算特殊情况,
可以补发。
穿过的人,都说不出它的味道:
不腥、不膻、不呕、不臭……
不似炝锅的老抽,
一种化学成分,
来自地底几千米的迸发。
石油人,有个“油鬼子”的别称,
具体是怎么来的,无从考证——
那些被我们用片石、铁皮、沙粒,
刮一片鱼鳞的成就感,
至今想起来,还是开心。
刮不完也搓不尽的油污,
让我前后裂隙的人生,
有了脱不开的粘连。
嚼沥青
嚼一块口香糖大小的沥青,
能嚼出幸福的童年。
爸爸妈妈的青春很短,
短到都不够往返戈壁的距离。
油田的孩子用一根橡皮
筋、一个布缝沙包、
一圈钢筋焊连的铁环、一把羊俾石
和废弃的烟纸,就能丰富留守的时光。
姐姐满口缺失的牙,
是不是嚼了太多沾牙的沥青?
是不是笑得过于开心,
忘掉太多的心酸?
一块硬沥青,能嚼出口香糖的声响,
能吐出比口香糖还大的泡泡,
能遮住疼过的智齿,爱过的虎牙,
贴心地呵护——
姐姐老了,如今看到我保存的一小块黑沥青,
裂开满口假牙的嘴,
孩子似地“呵呵”大笑。
燥热的天气,刹那就有了
湿润,有了瞬间的酸涩和安静。
铁铅笔盒
这该是我拆掉的第一根指骨。
抚摸字体的棱角和温度,记住
并学会运用到纸张和键盘的第一个伴当。
瘪下去的窝,是岁月的凹陷。
剥蚀的漆面,是记忆的缺失。
接触到的第一块铁和铅,
就源于它的馈赠。
一生唯一没有丢失的个性和品行,
就是折不下去的腰肌。
60年。不多,也不少。
它能让我像攥着爱情一样,满脸潮红。
马灯
第一个吹熄马灯的人,不是我!
再一次燃起光晕,把沙尘推开,
找到一行巡井小径的人,有我的参与。
白碱滩。多少忘不掉的经历,
让我们一起发痒。
一起给红肿的时光,涂上抚慰的药膏,
在梭梭草丛,数着钻塔挑开的星光。
擦拭落满烟尘和灰烬的灯罩,
像擦拭不易察觉到的疤痕。
辗转那么久,
岁月都无法把快要忘掉的事,
彻底掐灭。
戈壁、石油、偶尔跳过脑海的羚羊,
像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挂在嘴边,
就藏在心底——
采油女工
白碱浮起的采油树,
因为一个单薄的红色倩影而不再孤独。
撑不起的单工服和广袤的大戈壁,
像摊在桌面的A4纸,
等着第一个人生的笔画,
或延续的标点。
惬意的日子有无数繁星,闪烁
爱情的小谜题。
羸弱的月牙
有时比感情还要脆弱。
一棵挂满霜花的骆驼刺,
就能让青春的眼眶噙满泪光。
在新疆油田,
这样的画面堪比日落日出。
空旷的戈壁,缺少红色
嵌入的画面就不是风景。
石油密码
车过九区,昔日的白碱消耗了太多。
同时消耗的,是时光衰减的一段记忆。
形态各异的抽油机,
像一部厚重的石油史,
需要衔接的部分。
随意取的地名,沿用至今。
地表上,被钢铁占据的戈壁瘦得脱骨。
说过亿万年前,
这里的海水没想过
褪去颜色的人,
已经褪掉所有的功能。
城市里都碰不到几个熟人。
刚才给我指路的青年,
会不会是当年
一起漂过大箱的队友的后代?
轮廓隐约有石油的暗语,
有克拉玛依本地才可以破译的密码。
银行对面
是一所石油大学
银行对面是一所石油大学。
学子们正苦思冥想,
填写人生的正确答案。
我没有大学的履历,
技校胡混了两年,
就搭上钻井平台。
在上面晃荡着
西北辽阔的大好时光。
烤羊肉串的燎烟混浊了都塔尔的弦音,
一个身材曼妙的维吾尔族女孩,
让午后的太阳有了短暂的眩晕。
排队取钱的老人很多,
好像晚几天
就会少几张退休的保障。
一丝怅然让我不由自主加入衰老的行列。
所以,狮群里孤独离去的狮王,
让我流下堵也堵不住的悲怆——
轻声念出你的名字
接近零度。花朵委屈的样子
让我心疼。
秋霜清洗过的憔悴,
是我熬了一夜的诗句。
是满地揉搓的纸张
尚不能在键盘上,敲下第一组拼音。
西北以北,四个耳熟能详的字,
捆住我的手脚。比深夜更黑的石油,
给我比白昼更白的希望。
衣柜里,洗薄的红色工装,
码在那,流露不甘的表情。
抽屉里的团员证、党员证、各个学校的
毕业证;职工证、职称证、结婚证、
独生子女证和光荣退休证。一个个
码放整齐。每个证的封面都是红色,
字体有黑有黄,个别的烫着金箔。
我的一生就这么多。
再多,就盛不下了。克拉玛依!
轻声念出你的名字,就像从来都没有
自己把自己的姓名,从口中念过一样。
就像从来都没有人,
嫌弃过自己的长相一样。
在戈壁
谁的指令,让一只不知疲倦的鹰
在炙热的石头上,完成了蹲守。
翅膀下的戈壁,捂过了,会不会
孵出碧玉?
拱过石头的喙,再也甩不掉石英的硬度。
你听它腾空一呖,
像掏出胸腔内压抑过久的石卵。
翅膀拖走的风,挂住了
梭梭草和骆驼刺。
脆弱的露珠
还在守护太阳匀速地呼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