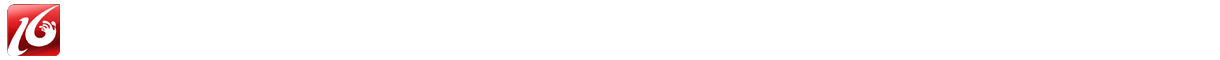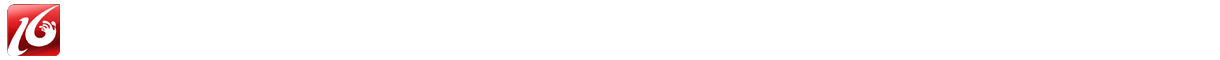老虎台探险
“自从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发现古楼兰废墟和新疆虎,并向世界发布之后,新疆虎和楼兰一样受到世人瞩目。1979年在印度召开的保护老虎的国际会议上宣布,作为里海虎分支的新疆虎已于1916年灭绝。由于没有一只新疆虎的个体留存人间,直至今天,人们还很难确定它的身份,加之最近几年不断传来新疆虎重现的传闻,人们对新疆虎的灭绝产生了疑问,也对新疆虎悬而未解之迷产生了好奇。”(《南方周末》2006年第309期)
我是坚信新疆有过老虎的。因为吐北一井所在的地方被叫作“老虎台”。
我们偶尔去离井场十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闲逛时,村里的维吾尔老人也会比画着告诉我们,他爷爷曾经在这里见到过老虎,比狼大一些,比熊小一些。并且说,军阀盛世才在新疆的时候老虎还出现过,但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了。
我和钻井监督张立春看着村子旁那座布满原始森林的深山,有了一种探险的冲动……
机会来了——井打到了设计井深,如何进行下步作业,要等上级主管部门的措施指令,我们有一个多星期的待命时间。我俩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老虎台山中探险。
我们让炊事班烙了十张牛肉大饼,装了一塑料袋咸菜。水不用多带,山里的泉水比什么水都好喝。
两人穿上运动鞋,带了两个看井时用的睡袋出发了。
为了养精蓄锐,我们第一天就住在了村子里的老乡家,准备第二天上山。晚上,老乡告诉我们,山里有熊,有时候会跑到村子里吃田里的玉米,而且晚上山里很冷。
我们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执意要去。老乡只好劝我们,见到没有羊蹄子印的地方,就不要走了。别遇到熊了。
伴着身后的朝阳,我们出发了。眼前一个小山头,我们打算一个小时翻过去,谁知道这种想法纯属蚂蚁撼树,我们一直走到中午还没有爬上山顶。
在松树林中,我们每人吃了一张肉饼,改变了一下行程计划:今天晚上在这座山头的另一侧宿营,明天进深山。
当最后一抹阳光从林梢退去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山脚下。抬眼望过去,挡在面前的是一座黑黢黢的更加高耸的山峰。稍有野外生存经验的张立春把宿营地选在了背坡向水的高地上——万一夜里有山洪,我们不会有大的危险。
我以后的“驴友”经历,其实就是从这次启蒙的。与大自然如此亲近的美好感觉,不是单位组织去乔尔玛旅游与之可以媲美的。
可能是太累了,本来换地方就难以入眠的我,居然早早地睡了过去。也不知什么时候,张立春把我拍醒了,“你听,熊叫!”
真的,从深山中传来了几声嘶吼,这声音在夜晚的山谷中回荡,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从声音判断,它距离我们很远。
即便这样,我们也不敢睡了,立刻收拾行囊,借着月光回头了。
都是省钱惹的祸
1999年,甘霖和我一起去准东地区的沙南油田打S111井。这口井是技术承包井,如果技术运用得当,节余的材料费全部都归钻研院所有。我们俩有了一个打好井之外的目标——为单位多挣钱。
日常生活中,我们俩都不是吝啬的人,但也许是邀功心切,也许是对自己的技术水平估计过高,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主要任务放在了“省钱”上。
在计划材料过程中,我们俩算了又算、减了又减,能够靠自己技术能力支持的环节,绝对不花钱。居然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应急的余地。
开钻了,本来应该使用坂土——CMC泥浆体系,我们却只用了四百元一吨的坂土,连一袋昂贵的CMC都没有加,甚至连两千多元一吨的烧碱都舍不得多用。两个人搬着一袋烧碱,在循环罐上来回走,像撒金子一样珍惜。一开井段,居然顺利地下了套管、固完了井。
在进行二开的配浆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做了不少实验,不为别的,就为了看能不能少用一些一万多元一吨的高分子聚合物。看着泥浆杯中性能不怎么样的样品,我们俩对视了一下,都咬了咬牙说,就按0.15%的含量加——按照这种地层的客观条件,稳妥的做法是要加入0.3%—0.5%的呀!
二开井段是快速钻进阶段,井队每天要打四五百米的进尺。我们俩把持着胶液维护罐,小孩撒尿一样地让像三年自然灾害时吃的稀米汤般的胶液流入循环罐,井队技术员来问我们,浓度这么低的胶液行不行呀?
我们俩心里打着鼓,却把胸脯拍得山响。
仅仅过了7个小时,出口泥浆开始发生变化了——流得越来越困难,如同孩子的腹泻物一般难看。
我和甘霖的心里都“咯噔”一下——坏了,高分子聚合物太少,没有抑制住地层粘土的侵污,再继续下去,井下可能要出事!
“玩过火了!”我开始后悔。“赶紧找队长,停钻,处理泥浆!”甘霖一溜烟跑着找队长去了。
队长马维成看到现场的情况,马上下令停止了钻进,并要求全队人员都配合我们进行泥浆处理。这本不是井队的工作,而且停钻一个小时,将对井队造成数千元的损失,但他却没有责怪我们一句。
把罐中的泥浆放掉了一半——放的时候,我在算钱:八万元没有了!
配制大量高浓度的处理液——配的时候,我在算钱:又多花了五万!
经过5个小时的紧急处理,终于又可以开钻了。而我和甘霖,以及全队的职工,都已经累得爬不起来了……
事后,马队长对我们说,看你们俩那“塞皮”样,不花钱就想打井?不过,如果咱们中国人都能像你们俩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那我们的建设成本和建设速度就会有质的变化!
盗挖大芸者的结局
在呼克公路75公里处有个右进岔路口,进去以后前行68公里,是新湖农场七分场,农场的棉花地紧挨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在起伏的沙丘中,蜿蜒着一条石子路,那是克拉玛依石油人为打盆参二井而修造的。顺着这条路前行11公里,就能看到一部低矮的井架和几间沙漠野营房,这是试油公司正在进行盆参二井的试油作业。
1999年,钻研院负责这口井的修井液技术服务,我被派往现场。
相对于钻井液技术服务,修井液配制维护的工作量和难度要小很多,驻地的噪音也小多了,因为修井机比钻机的马力要小得多,这次任务几乎成了我休养生息的机会。
1992年,我的井队工作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打的第一口井——盆参四井,就在离盆参二井不到10公里的地方。我打算步行去看看那片井场和那个我为之奋斗过的井口。
四月中旬的古尔班通古特天高气爽、草色返青,大芸也快要顶出沙面了。
大芸,又名肉苁蓉,维语叫“吐什干斋代克(意为兔子吃的胡萝卜)”,是多年寄生草本植物,常常生于沙漠中的梭梭、红柳、白剌、沙拐枣及蒿类等植物根部,依靠这些植物供给养料和水份。它在沙质土壤中,不见阳光能长到50公分至75公分。在地下生长时,没有叶,不进行光合作用,所以无叶绿素合成。出土后,抽苔的苗茎开始进行光合作用而合成叶绿素,使黄褐色的鳞片变成青紫色。
我们祖先很早就知道大芸可食用,而且有滋补的药物功能。《神农本草经》称其主治“五劳七伤,补中,除体中寒热痛,养五脏,强阴,益精气,妇人症瘕,夕服轻身”;《名医别录》言其“除膀胱邪气,腰痛,止痢”;《甄权药性本草》中有“益髓,悦颜色,治女人血崩,男人壮阳,大补益,主赤白下”的记载。
大芸“乃平补之剂,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泄,故有从容之名”。又因肉质肥厚,所以叫肉苁蓉。它还有金笋、地精和“沙漠人参”等高贵的别名,国家收购价很高。
大芸一般高度5—100厘米,圆柱形,药用的肉质茎春秋采挖,以春季出土前采挖的质量为好。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所产的大芸质量尤其好。每年的4月,就有不少来自新疆各地,甚至甘肃、青海、四川、河南的不法分子钻进沙漠,偷挖大芸。
在路边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一辆警车。
当我走近观察时,眼前的情景令我几乎作呕——
一具发黑的死尸几乎开始腐烂,死尸旁边,有水壶、铁锨和装着几根大芸的塑料编织袋。
死者是一个偷挖大芸的人。警察接到了当地群众的报案前来勘察现场,法医鉴定的结果是因急性病发作死亡。
死者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联系到其亲属的方式,警方从其着装、长相、身高和用具判断,这是一个从外省来的人。
不管怎样,死者要入土为安。七分场的领导安排部分团场职工就地挖了一个坑,将其裹上白布入葬。
一场风之后,这里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谁都不会知道这沙地之下有一副曾经鲜活的躯壳。也许他为了生计才千里奔波到此,挖些大芸换钱糊口。
但以这样的方式丧命于异乡,并且几乎没有了葬身之地,这样的生命不如草芥——无声无息,可悲可叹。
快乐的穴居生活
离盆参二井试油井场两公里的地方,堆放着全套的钻井设备。因为打完这口井的钻机没有新的井位,为了节省运输和库存费用,暂时搁置在这里。
老道和冬瓜负责看守这些设备。
我经常去找他俩玩,一来二去,发现我们彼此很投缘——都是在井队呆的人,性格豪爽、脾气相投。有了这两个兄弟,我也觉得在沙漠中不寂寞了。
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
生产和生活设备全都封存了,只留给他们一间野营房住宿;一个能盛装4方水的水罐和两个电瓶,用以开报话机汇报工作;点一盏5瓦的小灯泡。20天到一个月,上来一辆水车给他们卸点水,顺便把他们用完的电瓶换掉,另外带点大米、挂面和鸡蛋来。
相比而言,我的生活太“优越”了。因为单位定期不定期地给我送纯净水、清凉饮料和瓜果,在其中一段时间,还给我配了一辆值班车,有事随时都可以去150团场。
朴实的老道和冬瓜从来不主动让我帮忙。但我只要工作不忙,就会给他们送些东西来,如果要去150团办事,就把他们俩其中一位拉上去“放风”。
夏季的沙漠,地面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因为没电,他们的房子无法开启空调。机灵的冬瓜想了个招儿——挖地窖。
太阳落山以后,空气的温度允许人干活了,我们借着月光或点亮小灯泡,开始了类似原始人的“穴居建设工程”:在有土的硬地上,直接开出了面积三平米、深度一米五的方形坑,坑底铺上干燥洁净的沙子,然后在坑顶耽上钢管,铺上帆布,再在帆布上浇上水,用来阻挡白天帜热的阳光。
老道把被褥搬进了地窖,也给我搬了一套。白天,我们三个人躺在里面看书、睡觉、打“跑得快”——谁输了谁做饭。
你知道里面有多舒服吗?温度计显示,里面的温度是27摄氏度,而且很湿润,是因为帆布上有水的缘故。从此,我一有空就来享受一下,比我的空调野营房舒服多了。
有了“卧室”,我们就想搞“冰箱”了:在地窖侧面的底部开个洞,可以放蔬菜和肉,能放两天不坏。这样,老道和冬瓜就不用天天吃猪油汤挂面和蛋炒饭了。
于是,冬瓜有了展示自己厨艺的条件:大盘鸡、那仁、红烧肉,我们甚至还能每天喝到“冰镇”啤酒了。
最快乐的是每天晚上,我们拣来干梭梭柴,用自制的铁签烤肉,映着篝火高声唱歌——最寂寞的地方也有真实的快乐,因为有真情!
与狼同路
1999年,盆参二井的位置上,还没有移动电话信号,所以,我们打电话只能步行去8公里以外的三连连部,这8公里路程中,有7公里是没有人烟的沙漠。
7月的一个傍晚,一吃完饭,我就和冬瓜去三连。说说笑笑地,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给家里打完电话,在小商店门口吃了点烤肉、喝了点啤酒,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就打道回府。
大概走了有半个多小时,我们的左侧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借着月光,我俩都看清了,那是一条狼——粗尾巴垂着,后颈有鬃毛乍起,虽不是跑,但步态完全区别于狗,是一窜一窜地走。
它离我们有八九米远,眼睛盯着我们,在晃动脑袋的时候,会有绿光一闪一闪。
我俩顿时心里就毛了——因为是夏天,我们俩都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这条路是1991年修的沙石路,虽然铺路材料中有鹅卵石,但经过8年大车的碾压,那些石头根本就抠不出来,我身上唯一可以叫做武器的就是一个塑料打火机,虽然路边有低矮的梭梭,因为那年雨水多的缘故,根本找不到可以点火的枯枝。
我们尝试着心理战——突然停住,狼也停住;突然蹲下,猛地起来,狼不跑;快步走,狼也加快速度。
怎么办?在这危急时刻,还是显现出我们俩性别上的优势:短暂的慌张之后,马上镇定下来,并且在商议应对措施——
首先,我们不能以攻为守。因为我们俩都穿着拖鞋,行动不便,而且狼看到我们是两个人,没有绝好机会,它也不敢冒然出击。
但是,我们必须做好狼攻击我们的准备。我高瘦,冬瓜矮胖,而且冬瓜走在左侧,离狼近,我们俩一致认为如果狼要攻击,一定是首先攻击冬瓜。
所以,我俩都把汗衫脱下来,围在冬瓜的脖子上——狼的第一口一定是咬猎物的脖子,两件汗衫的厚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狼牙的致命攻击。如果狼扑向冬瓜,他就顺势倒地,我则扑到狼背上,掐狼的咽喉,然后两个人一起将其摁倒掐死。
一切考虑停当,我们反倒坦然了,故意大声唱歌——告诉对手,“我们不怕,有种就过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路边窜过一只野兔,向远处跑去,狼和我们同时发现,它毫不犹豫地向兔子追去。那伟大而英勇的兔子如箭一般把狼引开了,狼很快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外。
我俩几乎同时撒腿就跑,身体里似乎有无穷的力量,拖鞋和运动鞋也没有了丝毫的区别。一口气跑到了灯火阑珊处——我们亲切的井场。
晚上洗脚时才发现,我左脚大拇指外侧磨掉了一大块皮,一沾水生疼。呵呵,跑的时候可是一点也没感觉到呀!
第二次车祸
钻井人,是一群离家的人。我们主要的工作生活场所是戈壁和沙漠,我们坐车出行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城里的人。所以,出车祸的概率也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1996年,那次几乎要了我的命的车祸,让我对生活和生命有了全新的定义。所以,三年之后的这第二次车祸,只在我心中留下了微小的涟漪。
那天,我们的车行至呼克公路黄沙梁子,已是下午4时了。有了第一次车祸的经验,我以后坐车都尽量不睡觉了,因为人在清醒状态下,处理突发情况的反应速度,要比完全放松状态时快得多。
又是一次超车,不过,前方是个大弯道。
当我们的车从前车左侧探出头时,我和司机同时看见迎面来了一辆车,不过距离并不近。及时刹车是不会有大危险的。
司机在第一时间踩下了刹车踏板,但车的方向完全失去了控制——后来才知道,前几天才送到相关厂子保养过的车,没有进行必要的试车环节,左右两个制动刹车片“偏刹”。
我们只能无奈地和车一起栽下了路旁的芦苇荡。在一两秒钟的时间里,我做出一系列准备动作:双脚死死顶住前挡板;双手抓住了司机的方向盘;咬紧了牙关,避免口腔受伤。
我们的车毫不犹豫地侧翻在芦苇荡中,在最后一下震荡之后,我立刻睁开了眼睛——
我压在司机身上,额头在流血。我立刻站在他身上,打开了目前在我头顶上的右侧车门,爬了出去,紧接着司机也爬了出来。
我们到路对面的泵站去求救,油气储运公司两位漂亮的女工赶紧拿来了棉花纱布之类的东西,并给我们单位打了电话。
司机掏出100块钱,在路上拦了一辆车,让我先走,赶紧去医院,我的小腿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口子。他因为被我压着,没有受外伤。
两次车祸,在我身上留下了四五处伤疤。后来,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洗澡,保加利亚人兹姆法尔看着我身上的伤疤,钦佩地问:“你经历过战争?”
我笑了笑说:“不一定只有战争才能给人以难忘的经历。”
吃饺子
那是1995年,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又一次连续工作了3个月。跟我合作的这个井队和生活服务组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些老兄们别的都不吃,天天顿顿都要吃米饭。
按说,我并不讨厌米饭,但架不住一口气连续吃270顿呀!
那时候,我想面食都快想疯了。
终于盼到换班的时间,一到库尔勒,基地经理任凤君就带上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去一家听说挺实惠的山东饺子馆。
实惠,的确名不虚传,饺子个儿大馅儿足;味道,也和家里包的一样地道;更由于连续吃270顿米饭的“惨痛经历”,我甩开了腮帮子……
任经理帮我数着,结果我一口气吃掉了80个韭菜羊肉饺子。真舒服,还是俺们北方人的饭好吃。我打着嗝把皮带放到了最后一个扣。
我们晃晃悠悠地散步回到塔一勘基地的房间,任经理叫大家打牌。就在我刚摸上一把“封门儿”的好牌时,肚子在一秒钟之内剧痛起来。
我连声都来不及吭,就一下跪倒在地上。我还听见对面的阿柄调侃我:“哎,还没过年呢!”
马上,大家都感觉不对头了。“发动车,快去医院!”老任催促司机,同时让身高一米八六、体重110公斤的于小健背上身高一米八三、体重80公斤的我。
塔指医院的医生起初怀疑我是阑尾炎、胆囊炎、胃穿孔之类,但经过一系列检查,全都排除了。“这小伙子吃得太多,撑着了!”医生最后下了结论。输了一瓶液体,只输到一半,肚子几乎就不疼了。
刚好那天医院没有几个病人,输液的时候,我就和医生聊起天来。从他口中,我懂得了一些很重要的养生理论——
人的身体,就如同一张纸。刚出生时,健康的婴儿就像一张全新的白纸,没有任何损伤。得一次病,就好像在这张纸上折一下。就算治好了,折痕也不能完全消除,如果总是得一种病,也就相当于在同一个位置来回折,总有一天会完全折断的。所以,别看有些人身高体壮,如果不注意正确的作息规律,得了病不及时治疗并注意保健,就会突然因为一个看似很小的毛病死去。
而为什么有的人浑身是病,但寿命还挺长呢?那就相当于在这张纸上到处折,折来折去,把一张硬纸折成了一张“卫生纸”,到处是皱纹,但小心点拿,它也不破。可是它经不起风吹雨打了,很脆弱。
由此,我想到了更多的内涵——
如果在这张纸上写下《资治通鉴》,那这张纸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如果在这张纸上画出《向日葵》,那它就是一件流传百世的艺术品了;可以写下对爱人的情书;可以表述对理想的追求……
当然,你也可以在上面涂鸦;还可以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可以将不该公布的秘密传递……
不过,那还不如让它永远是白纸一张来得纯洁……
他被狼咬了屁股
从试油公司后面农场的油田公路前行140公里,就到了石西、莫北油田的检查站。在检查站右手边有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沙石路。这条路曾经是2000至2002年莫北油田会战时的“功勋路”。我们打MB04水平井时,井队的拉水车就每天往返于这条路。
路左侧是连绵起伏的沙包,右侧是生长着比较茂密沙漠植被的沟底。这片沙漠本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石油工人的“入侵”,似乎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和心情……
司机老秦的活儿挺单纯——一天两趟地往返于这条沙石路上,给井队拉生活和工业用水,顺便给工人们捎带点儿烟和零食。
7月的太阳已经落山了,水车还没到,我还等水配制泥浆用的胶液呢。心里在埋怨老秦:“这个老家伙,干什么去了?”
当夜色完全笼罩了井场的时候,老秦的“斯太尔”车那熟悉的灯光才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但从车的“步态”看,好像有点“喝高”了。
车一停,老秦就猛地打开车门,把车钥匙扔给我,手捂着屁股痛苦地说:“你自己摆车吧,我找医生去……”
在医务室里,我才知道了他裤子上鲜血的来由——
老秦拉上水,在沙石路上走了十多公里,中午的拌面消化好了,想下车“方便”一下。他知道这一带有野兽,就没敢走远,头冲里蹲在车前轮旁边“使劲”。
论嗅觉,狼比狗强,再加上老秦的肠胃蠕动差点儿,这秽物的气息在广袤的沙漠中飘散得就相当悠远。
在老秦用手指头在地上瞎划的工夫,屁股突然一下剧痛,他的头皮几乎都要麻醉了。他转头一看,是一只狼!
他已经来不及提裤子了,对着狼一声嚎叫,把那家伙吓退了好几步。光着屁股冲进驾驶室把门锁上了。
真难为老秦了——两道深深的血口子,皮肉尽翻。他就这样坚持把车又开了十多公里回到了井场。
后来,老秦逢人便讲,在野外“方便”时,最好爬到车顶上去。我就糟蹋他:“你个老家伙懂啥,如果真来了野兽,你怎么从车上下来?”因为我曾经遭遇野猪的经历比他还惊险呢!
探亲
“刘师傅,我未婚妻说明天想上井来看我,你看行不行?”朱丹宏腼腆地问我。
“好事呀!领证了没有?领证了我就给你们腾房子!”我逗他。
小朱是200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我们单位的,工作积极主动,学习态度认真,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喜爱。大学里谈的女朋友也随他来到了克拉玛依,在克石化厂工作。
因为我们单位工作性质的原因,热恋中的这对年轻人聚少离多。这口井在乌尔禾,离克拉玛依很近,他的未婚妻小张想利用休息时间上井看看他。
傍晚,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今天我回去一趟,领点材料,明天上午把小张接来。”主任嘱咐我:“那明天你就别当电灯泡了,呵呵。”
不到100公里的路,让小张急不可待,嘴上说不着急,可眼睛一直在找井架。不解风情的司机木沙江说:“刘工,我们先到乌尔禾吃饭吧,吃完再上井。”
“不行,先把小张送到井队,然后我们俩出来吃饭。”
回到井场的野营房一看,朱丹宏把房子从里到外清扫一新,还摘了些野花放在床头柜上,在我床头放了一包“玉溪”。
“这小子,还挺爱面子!”我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的“美登”,真想笑出来。
我早已想好全天的安排了——
“小朱,换上喝茶的衣服,等一会让木沙江拉你们去魔鬼城,小张刚来克拉玛依,没见过;然后,去风城高库看看,那一路的胡杨林特漂亮。我在井上看着。”
“不了,师傅,她就来看看我。一会就让她走吧,下午井上也有工作。”
“井上的事不用你管!”
正在我们俩“争执”的时候,井队队长许志勇跑来了,“美女!美女!谁的美女来了?”
知道情况后,许队长对我说:“刘工,下午就是正常打钻。没啥事,你也出去玩吧!有事我给你打电话请教就行了!”
这家伙简直和木沙江一样不解风情。
这下小朱有借口了,“那一起去吧!”
在魔鬼城,我有意拉着木沙江走在前面。但他居然回头喊:“快看,前面那个土堆像不像骆驼?”我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
在胡杨林中,这个第一次来新疆的东北女孩儿被金黄色的绚烂陶醉了。就在她含情脉脉地望着小朱的一瞬间,我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傍晚,小张走了。
我好几天都在叹息——人家两个人因为我们这些“电灯泡”,连手都没拉一下。木沙江说:“什么呀!我们俩到树林里撒尿的时候,两个人的嘴马上贴上了,我回头看见了!”
他的屁股上又挨了我一脚。
狗给工程师送羊肉
我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巴郎子”,当然喜欢吃羊肉。不过2004年在塔河油田打的S115井,却让我和同样爱吃羊肉的曹阳痛苦了好几个月——井队是从江汉油田来的,他们全都不吃羊肉,所以也不做羊肉。
塔河油田钻井市场实行项目承包制,现场作业过程中的责任、岗位分得很清楚。我和曹阳是钻井泥浆技术承包单位的现场负责人,我们以主、副岗工程师的身份,根据设计要求给井队下技术作业指令。
这活儿,如果碰上复杂井、难度井或者快速钻进阶段,的确很辛苦,责任也大。可这S115井的五开井段是石炭系地层,通俗地说,就是在坚硬、结实的石头上钻眼儿。这对于我们现场泥浆技术工作来说,真是太舒服了——井下几乎没有发生复杂情况的可能。
在工人们辛勤劳作的时候,能陪伴我俩打发无聊时光的伴侣就是井队上以淘汰军犬大黑为首的三条狗了。
大黑“军旅出身”,虽然因超龄“转业”了,但那种好战的欲望一点都没有减弱。它厌恶炊事班职工给它准备好的饭食,整天带着黄黄和阿白抓野兔吃。
因为它们的带路,我和曹阳在胡杨林和周围的沼泽中发现了不少好玩的去处,曹阳甚至还看见过马鹿。
麦当村离井场有5公里远。这天我们带着大黑它们去玩。
在大黑眼里,村子里的狗全都是“羊”,加上它好斗的天性,将那十多条企图阻止大黑进入其领地的土狗收拾得服服帖帖。
这次串门之后,大黑就经常独自带着黄黄和阿白到村子里“嚣张”。
一天上午,我刚从循环罐上下来,看到两名拉着一辆平板车的维族老乡在和井队队长说话。走近才看清楚,那平板车上,躺着六只大小不一的死羊,全部都是因咽喉被咬断而死。
原来,大黑吃兔子不过瘾了,趁着夜色,带上黄黄和阿白袭击了一个老乡的羊圈。老乡知道是井队的狗干的,来找队长要赔偿。
只有给人家钱了,井队掏了1200元买下了这六只死羊。队长掏钱的时候,已经被铁链锁住的大黑仍然打算袭击老乡。
炊事班中午做了一道菜:羊扒。别看湖北人不吃羊肉,烹调出来的羊肉味道还不错。由于其他人全都不吃,那只有我和曹阳消耗了。这六只羊,直到我俩换班离开时,都没有吃完。
从那次事件以后,大黑被套上了铁链,铁链的另一头挂着一只十多公斤重的废铁闸门。我和曹阳经常帮着大黑搬起那闸门,让它能轻松地跑一会,但抓兔子的事,它是想也别想了。
井喷
井喷,是因为所使用的钻井液密度未能平衡住地层中油气水的压力,而造成油气水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喷出井口。
井喷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预防措施不周全,处置手段不当,很容易造成井喷失控起火、硫化氢气体外泄,导致井毁人亡的惨剧。
一般情况下,对地层情况已经非常清楚的生产井不容易发生井喷,因为地层中流体的压力已经很清楚了,在钻井液使用和井口防喷设备方面,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
而预探井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地下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发生井喷的概率就要大得多。
2004年,我和曹阳在塔里木河边上打的那口S115井,就是一口预探井。
当时井深5000多米,已经接近了设计目的层,随时都有可能有油气显示。全队上下都做好了预防井喷的准备——储备高密度钻井液、检查井口防喷器、每个星期组织两三次防喷演习,主管安全的副队长甚至还弄了只身高体壮的公鸡“把守”在井口——一旦出现硫化氢气体,它将用“以身殉职”的方式来报警。
和地震一样,井喷有时也会有前兆。有经验的“老石油”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判断出井喷有可能发生。
我已经有十多年的井队现场工作经验了,经历的井涌和井喷威胁也不止一两次了,所以,作为现场主岗工程师,就格外注意观察井口的动静。
那年的一天上午,井队在正常起下钻。我照例在循环罐上巡查,发现从井口出口导管不间断地往外流淌着一小股细细的泥浆流,我马上让当班泥浆工测量罐内钻井液体积——多出了0.25立方米。
这不是正常现象!我马上将这一情况通报给驻井监督和井队领导,要求当班岗位工人密切观察,并做好一切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
7个小时过去了,钻具下到了井底。就在司钻鸣笛让泵房开泵的同时,一股褐色的泥浆流一下从井口喷了出来,直接冲上了距钻台20多米高的二层台!
这个井队是从江汉油田来新疆塔河油田打井的,出外闯市场,挑选的人应当都是精兵强将,但那一瞬间,钻台上所有的钻工都吓傻了,没命地往钻台下面跑。司钻发出一声长笛鸣的指令,也几乎没有人执行。
只有井队工程师和副队长还算冷静,一人跑到一个防喷器手动控制阀处锁紧了防喷闸板。整个过程,超过了一分钟。
随着质量体系管理的运行,钻井现场工作分工明确,在这样的场合,我们这些技术服务部门的人员不能参与这个工作,因为那些地方不是我们的岗位。
但我在第一时间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惊心动魄的场面。
防喷器关死以后,我把摄像机扔给曹阳,冲到节流循环阀门处,让惊魂未定的工人们赶紧按照操作程序求压、取数据,以便为马上将要进行的压井作业提供第一手资料。
节流管线刚刚打开,带着强大压力的、混合着原油和天然气的钻井液就冲进了循环罐。泥浆工小蒲马上跑过去用铁锨去铲溅在罐面上的钻井液。
我着急了,大喊着:“滚开!可能有硫化氢!赶紧分离点火!”
唉!回想起199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盆参四井(就在目前的莫深一井旁边)也发生过井涌现象,当时,新疆石油局钻井探井公司6046队的司钻“田大刀”一声长笛,7名钻工各就各位,仅仅在15秒内,就制服了企图发威的气龙。等队领导和技术员赶到时已经开始压井作业了。
经常在《新疆石油报》上看到,“我局是……典范”、“克拉玛依……名列前茅”、“克拉玛依油田……领先”。以前对这样的新闻标题总是不以为然——自吹自擂吧?
但通过这两次处置井喷事件的比较,我要说,我骄傲,我是克拉玛依石油人!
石油人自拍DV
2004年,我和古清顺一起上塔河油田TK403井。他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到哪都背着照相机和摄像机,而我喜欢写点东西。
我们俩这种爱好上的互补,在打这口井的两个月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我们要是把井队生活的特点浓缩在一天时间里,用某种手法表现出来,那该多好?”
“对呀!照相?摄像?还是文字?”
“结合起来如何?”“怎么结合?”“拍DV呀!”“穿衣服,马上干!”DV名称:平凡的世界策划:古清顺编剧:刘亚峰导演:刘亚峰摄像(指导):古清顺演员:……(争执中)
我说我形象不好,由他来演;他说他面对镜头就紧张,由我来演。
最后,由于我摄像水平不过关,还是他摄像,我当演员。
剧情介绍:以记实的手法,表现一名工程师在钻井现场真实而平凡的一天,期间用具体细节反映出石油人的奉献精神。
镜头——
10月1日清晨,启明星还没有褪去,我穿上棉衣,哈着气走出了野营房,向着自己的岗位——泥浆罐和钻台走去。
钻机轰鸣,钻杆飞转,远处驻地的狗和鸡都还没有醒来。
我检查了报表和泥浆性能,舀了一缸泥浆做测试,特写镜头展现出我眼中的血丝。
给岗位工人写技术指令,烟灰缸的烟头已经满满的了,我的手指是被熏黄了的。
我蹲在井场上,用大海碗和工人们一起吃早饭,眼睛还在瞄着旋转的钻杆。
我用手机给1000公里之外的单位打电话汇报工作,对方告知,单位给“十一”期间坚守岗位的职工发了慰问品,说很羡慕。我说,要不你上来,我回去,慰问品你领。
中午,我已经穿上了背心在井场忙碌。毒热的阳光让胡杨树叶子打蔫儿了,狗也伸着舌头喘着粗气。
傍晚,在夕阳下土黄色的沙丘上,我穿着鲜红的工衣给妻子打电话:明天我要去轮台领材料,这样就和你只相隔940公里了,近了60公里。镜头慢慢从我头顶滑过,推向远处的两棵遥遥相望的胡杨树。
镜头叠进——夕阳中我站立的剪影;镜头叠进——星光和钻塔灯光中,我和钻工们忙碌的身影。
画外音(古清顺):日月更替,钻井人不息;星光灿烂,却内心平静;寂寞无声,虽钻机轰鸣。一个平凡的,对,很平凡的世界。
和老外斗法
2005年,中石化的塔河油田TK119HW水平井要采用地质导向钻井技术。这是目前国际上一种非常先进的钻井技术,只有几家外国公司掌握着。
通过谈判,法国的A公司和中石化塔河油田达成协议,负责这口井的地质导向钻井服务。
地质导向技术,对于井场设备和泥浆性能要求非常高。其中最主要的是循环系统不能“抽空气”,泥浆不能有气泡。当然,地质导向技术的实施者和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也要高。
井场设备由中石化四普大队的一支钻井队提供,泥浆由我带领着杨吉祥负责,A公司的水平井工程师、50多岁的新西兰人托尼带领着几名女博士、硕士和翻译进行地质导向技术服务。
开钻前,我非常谨慎,将泥浆调理得几乎没有瑕疵;井队也将整个循环系统的设备地毯式地检修了一遍。
一开钻,我和从新疆石油局借调到中石化的现场监督赵长青都感觉到托尼的技术能力有问题:简单的套管开窗就已经让他难以应付了;而四普钻井队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仍然将A公司奉若神灵。
现场配合工作不出事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出事,就容易扯皮——
当用了设计工期8倍的时间终于开窗侧钻成功之后,A公司先进的地质导向仪器传输不出井下信号了!这意味着装在钻头上、能够带领钻头找油层的“狗鼻子”完全失去了嗅觉。
托尼向甲方汇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类,一是设备“抽空气”,二是泥浆中有气泡。当甲方问他有没有可能你们的仪器有故障时,托尼涨红着脸拍着胸膛说:绝对不可能,A公司的仪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多年的现场工作炼就了我未雨绸缪的工作态度,我马上和小杨将泥浆性能全部重新检查了一遍——几乎和教科书中的标准一样。
井队也重新检查了设备,什么都没有发现。不过井队多了一项工作——天天请托尼等人吃饭。
不出我所料,两天之后,井队和托尼微笑着将矛头指向了我的泥浆技术工作,用完全非专业的语句,操着礼貌而探询式的问话要我看看泥浆有没有改进的可能。
“这是一种侮辱和阴谋!”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样。在现场作业时,泥浆工作人员最少,发生矛盾时,势力最单薄,但我决定应战。
井队的人好对付,但托尼是一个有20多年水平井现场工作经验的老工程师,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打过井,语言又不通,翻译还是他自己的人,我决定用其他方法打击他的气焰——
“托尼,我们都是学工科的人,都有比较强的逆向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我看看你这方面的能力如何?”我微笑着对他说。
“怎么看?”他做出一种长辈式的表情宽容而慈祥地回答。
“咬一口苹果,发现了一条虫子很恶心是吗?那么,发现多少条虫子最恶心?”
“……9条。”他迟疑了一会,自信而坚定地回答我。
“为什么?”
“你说的问题,是一个中国式智慧的问题。中国人以9为最多。”
“这小子懂得还不少!”我暗暗地笑。“我很欣赏你对中国文化的钻研,不过答案是错的,应当是半只。”我抽了一口烟,眯着眼睛向他微笑。
会议室里爆笑不止,托尼的白脸红起来。
扯皮已经20多天了,进尺只有十几米。最着急的是甲方,一天要付给A公司几万美元呀!
但甲方也搞不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最后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换新疆石油局钻井工艺研究院定向井公司的仪器试一下。
仪器一下去,计算机终端显示信号非常明显,井队设备和我的泥浆一点问题都没有……
A公司灰溜溜地撤了。托尼背包走的时候,我正好坐车路过他身边,我让司机将车速放慢,伸出头深情而真诚地用我发音最标准的一句英语对他说了一声:“good luck(祝你好运)!”
钻井工程师当了新闻记者
2004年10月,我从南疆换班回到了克拉玛依。一天,在办公室里,我随手翻开一张过期的《新疆石油报》,发现有一则招聘启示——该报要招记者。但再一看日期,报名早就截止了。
晚上,同事王凤军带着孩子到我家来玩。闲谈中,我问他:“你媳妇现在咋样?”
“刘青惠调到报社去了,正在集中培训呢!”
一天之中遇到了两个相关的信息,刺激了我的大脑——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记者,因为在我眼中,记者是高高在上、令我无比仰慕的人,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深邃,谈话高屋建瓴,下笔从容有度。
“其实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都有一定的格式,如果要当一个比较称职的记者,只要下点功夫,不是很难。但如果要当个大记者,就难了!”刘青惠来我家时,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一直喜欢看报,特别是新创刊的《克拉玛依日报》,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感觉:似乎一夜之间,我不再生活在克拉玛依矿区,而真正地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了。我喜欢这份报纸,有时候会从版面上挑点文字错误,然后给编辑部打电话。
“当记者”,这个念头似乎成了一见钟情的美女,之前想都没想过,但第一次接触之后,就无法遏止地爱上了她。
我开始审视自己:论知识面,从4岁背诵三字经开始,就把书着迷了30年,各方面的知识,我多少都了解一点;论经历,我搞科研技术和现场生产工作的同时还附带独立公关、协调和管理,出国留学过,摆摊卖过衣服,在歌厅、酒吧、晚会和广播电台当过歌手和主持人;论社会关系,我的交往圈当中,既有博士、专家,也有劳改释放人员;论文字水平,虽然没有发表过什么铅字,但拿笔和拿烟一样,都上瘾了。
最主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头顶上有两个“旋儿”——非常拧。只要我看上的,一定要拿下;只要我上手的,一定要最好!
可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因为上井而错过了报名时间。
还没有等我进一步考虑,又上井了。但这次上井,心情就没有原来那么平和了——总是幻想着自己拿着采访本、端着照相机到井队采访的情景。
我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经常骑出几百公里。一名克拉玛依日报社的记者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叫蒋剑。
我和他很投缘,有一次,我随口问他,报社还要不要人了,有机会告诉我一声。我说这句话本没带多少希望,但他却记在心里了。
2005年10月22日,我正在“精细勘探”的克115井忙活,蒋剑打来电话:“报社又要进人了,不过一般都要30岁以下的。要不你找社长试试看?”
下午固井,我抽空回了趟家,把我在网络论坛里发过的几个好一点的帖子打印了几份,直接敲响了报社社长唐跃培办公室的门。
“文笔不错。但写新闻和文学创作是根本不同的。你能不能写几个消息拿来我看看?”唐社长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消息?消息应当是把最主要信息放在第一段写,越往后越不重要的那种写法吧。”我暗自揣测。
翻了翻报纸,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写什么呢?就写我这口井出油的事吧。
3小时后,《克115井顺利完钻石炭系储层有新发现》的“考卷”交到了唐社长的办公室。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唐社长看了之后这样问我。
“您要是不相信,我当场再写一个。”心花怒放的我一脸平静而更加自信地回答道。
2005年11月21日,白14井成了我作为钻井工程师打的最后一口井——“社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调到克拉玛依日报社。”是唐社长的电话。接电话时,我正在进行完井收尾工作。
2006年7月25日,我到即将开钻的莫深一井采访,工人们正在摆放化工材料,我抓拍照片时,发现他们的摆放方法有点问题,忍不住上前说:“坂土、纯碱和烧碱应当摆到最靠近加重漏斗的位置,因为配泥浆最先用到的是这三种材料。”
工人们很诧异:“记者,你怎么这么清楚?”
我微微地笑了一下,转过身,凝望了一眼高耸入云的井架,走开了……